肖伏根,44歲,系吉安市青原區東固畬族鄉東固村委會舍下村小組人,靠務農和經營石灰精廠為生。筆者與他是同鄉,以前經常目睹他和他的父親在東固街上擺攤刻圖章。去年年底,筆者想寫一篇關于刻圖章的文章,登門拜訪了肖伏根。在采訪中,肖伏根說他們以前不但會刻圖章,而且還會刻活字,用祖傳的方法給各姓氏造族譜。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這就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木活字印刷術啊!

肖師傅現場演示

肖伏根夫婦把字模盤進行綁扎

散發著墨香的成品

字模盤積滿了灰塵
據查資料得知,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經過長期實踐和研究才發明的。自從漢朝發明紙以后,書寫材料比起過去用的甲骨、簡牘、金石和縑帛要輕便、經濟得多,但是抄寫書籍還是非常費時費工,遠遠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至東漢末年的熹平年間(公元172年—178年),出現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大約在公元600年的隋朝,人們從刻印章中得到啟發,在人類歷史上最早發明了雕版印刷術。
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業發展到全盛時期。北宋平民發明家畢升總結了歷代雕版印刷的豐富的實踐經驗,經過反復試驗,在宋仁宗慶歷年間(公元1041年-1048年)制成了膠泥活字,實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項重大的革命。活字印刷技術流傳到了元代,有一位農學家叫王禎(1271年—1368年),字伯善,山東東平人,他給后世留下了一部總結古代農業生產經驗的著作———《農書》。王禎對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選字、排字、印刷等方法寫了詳細的總結,題為“造活字印書法”于《農書》雕版印本的后面公布了。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他在安徽旌德請工匠刻木活字3萬多個,試印了6萬多字的《旌德縣志》,不到一個月就印了一百部,這在當時來講,效率是很高的。王禎發明的木活字印刷術的主要方法是:在木板上刻好陽文反字之后,鋸成單字,用刀修齊,統一大小高低,然后排字,行間隔以竹片,排滿一版框,用小竹片墊平并塞緊后涂墨鋪紙刷印。明代之后,木活字印刷逐漸發展起來。
明代的木活字本較多,不論是官府還是民間的書院、私人均曾用木活字版印書。在清代,木活字技術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獲得空前的發展。大規模用木活字印書則始于清乾隆年間《英武殿聚珍版叢書》的發行。從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36年)開始,武英殿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木活字印刷。經過三年的工作,共刻制了大小兩幅活字,共計25萬多個,并試印了30余種書籍。在取得經驗的基礎上,正式印刷了《四庫全書》及其它經典著作,幾乎包括了經、史、子、集等歷代的重要著作,其印刷圖書的數量,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次印刷。由于乾隆皇帝為木活字版取了“聚珍版”的雅名,因此,這次印刷的書籍統稱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印制該書共刻成大小棗木活字253500個,印成《英武殿聚珍版叢書》134種,2389卷。
在清朝時,木活字制作家譜幾乎流行于整個南方。
新中國成立之后,特別在“文革”時期,木活字印刷受到很大的沖擊。改革開放以后,因電腦排版印刷的普及和現代印刷技術的發展,這一古老的技藝已經淡出歷史舞臺,瀕臨失傳。目前,在全國保留下來的極少,在我省猶如鳳毛麟角,屈指可數,而在吉安市可謂絕無僅有。201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中國活字印刷術列為“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閑話少敘,言歸正傳。筆者進一步追問他這些活字和印刷工具還在嗎?他漫不經心地說,有這些東西又有什么用?如今搞這一行不要說賺錢,連吃飯的錢都尋不到,共有幾萬字模連同其他家什丟在老屋樓上,已經有20多年了。筆者迫不及待請他帶去看看。筆者對這間老屋的印象很深,因為以前其門額上寫有“相國第”三個筆酣墨飽的大字,惹得凡從門前經過的人,都投去驚奇的眼光。經詢問肖伏根的父親肖聚文才知道,原來漢高祖劉邦的丞相肖何是他們的遠代祖宗,他們以此為榮,故名“相國第”。如今,“相國第”三字不見了,門額刷新為“永聚文光”四字,別出心裁地把肖聚文的名字鑲嵌在中間。老屋顯得老態龍鐘,墻體還有幾處裂縫,但廳堂裝飾得古色古香,頗顯書香門第風范。
沿著踏板樓梯上了樓,眼前一片漆黑。借著手機的光亮,看到傍著墻壁高高地壘著層層疊疊的,像端菜的托盤一樣的木盤。肖師傅告訴我,這些木盤里裝的是字模,共有幾萬個。定睛一看,見這些陳舊的盤子上積滿了灰塵,用棕刷刷干凈之后便顯出密密麻麻、排列整齊、黝黑的字模。如此彌足珍貴的非遺文物,竟置之不見天日的危樓,塵封數十載無人知曉,真是可惜!可嘆!
慨嘆之余,向肖伏根“追根求源”。原來他家祖居陂頭(渼陂),雕刻印章是他家歷代祖傳技藝。清末時期,他的曾祖父與人合伙雕刻了幾萬字模,開辦了一家譜局,為各姓氏造譜,并一代接一代傳承下來,至肖伏根已是第四代了。1958年,東固派出所和當地政府邀請肖聚文來東固刻印章。肖聚文見東固是個富庶之地,便舉家遷來東固定居,除了刻印章,還要兼顧譜局的工作。直到上世紀“文革”期間,族譜被當成“四舊”燒毀,譜局被迫解散。
改革開放以后,修譜、續譜又在民間興起,肖聚文他們又恢復了譜局。可是,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造譜也圖捷便,把譜稿交付鉛印。至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譜局完全沒有了生意,無奈,只好“打狗散場”。肖聚文就把這些不能賴以養家糊口,毫無用處的字模和工具堆放在樓上,靠種責任田和刻印章度日。他這一堆,這些字模和家什就在黑暗塵封中呆了20多年,他自己也已去世好幾年了。
筆者根據肖伏根的講述,寫了一篇《手工造譜》的文章,在井岡山報“廬陵風”發表后,引起了青原區政協和有關部門以及東固鄉黨委的重視。今年的二月二廟會暨青原區廬陵文化旅游節前夕,區政協和鄉黨委作出決定,要把木活字印刷術在旅游節上進行首次展示。區領導委托筆者把這一消息轉告肖伏根。肖伏根說要展示并非容易,一是字模不能淋雨,要在室內進行,并且要有寬大的場所,才能擺得下幾萬字模。二是憑他們兩夫妻,要把幾擔沉重的字模和家什從樓上搬下來確實很困難,需派人前來幫忙。這些都得到了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農歷二月初一,鄉政府一行五人由筆者當向導,來到地處偏僻的肖伏根家。肖伏根夫婦將一盤一盤的字模裝在木夾里,然后頗費力氣地一夾一夾從樓上扛下來,再裝上三輪車,運至知青文化創意園展示廳。
翌日,肖伏根為游客完整地再現了古代木活字印刷的作業場景:寫繁體反字、刻字、揀字、排版、校對、印刷等工序。至此,塵封二十余年,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木活字印刷術,終于重見天日,一展風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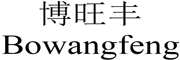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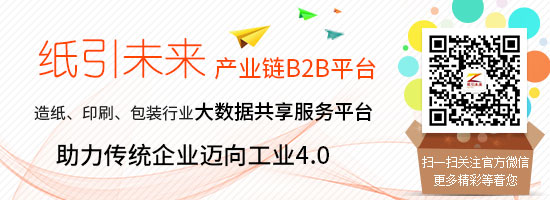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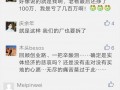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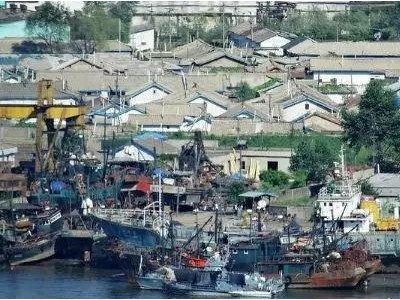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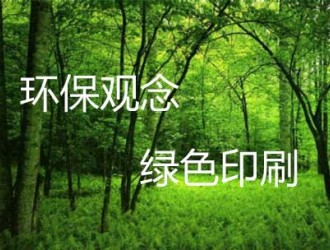


 紙友
紙友
 行情
行情
 訂單
訂單
 廣告
廣告
 找貨
找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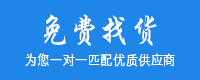
 簽到
簽到

 關注
關注
 客服
客服 TOP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