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聲書2016呈黑馬姿態
有聲書近年來屢被看作出版業的“下一個出版重點”,2016年終于不負眾望,以黑馬姿態成為增速最快的出版門類之一。
在美國、歐洲,有聲書“閱讀量”已被計入國民人均年閱讀量統計。根據美國有聲書出版協會(APA)公布的數據,截至目前,全球有聲書市場價值已超過28億美元,僅新書的數量就達到4.3萬種。而放眼國內,據易觀智庫相關統計顯示,目前國內有200多家聽書網站,近200款有聲聽書類APP,一些電子書閱讀軟件也紛紛添加“聽書”功能,有聲用戶規模已突破1.3億。2015年我國有聲閱讀市場規模已達16.6億元,同比增長29.0%,其中電信運營商的收入就將近3億元,預測2016年該市場規模將達到22億元,3年內將達到百億元。
與此同時,有聲書也成為政府大力扶持的文化項目,如朗聲公司的朗聲數字聽書館2015年入選國家新聞出版改革發展項目庫,引導文字版權人、播講者、音樂創作者、錄音制作者、傳統出版發行人、讀者等各方參與者進入“數字聽讀時代”。在2016深圳文博會上,朗聲公司帶去了其數字聽書館制作的四大名著有聲書。朗聲圖書負責人歐陽群表示,在數字出版領域,有聲書的出版將是未來的一個趨勢,尤其是基于移動互聯網的數字化有聲書平臺正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而從投資的角度看,一方面,國內出版的圖書轉化為有聲書的比例不到30%,相較國外的60%~70%比例,有聲書在國內上升的空間非常大;另一方面,有聲書所帶來的盈利也是可觀的,北京廣播電臺旗下北京悅庫時光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張蓉告訴記者,“我們對喜馬拉雅、蜻蜓、考拉這些音頻APP平臺做過調研,發現有40%~50%的流量都是有聲書帶去的”。她認為,有聲圖書發揮的作用可能不是短期的峰值,但一定是“長尾效應”。對此,酷聽聽書副總裁于琦表示贊同,“數據顯示:聽書類平臺上超過70%的粘性用戶來源于有聲讀物,而不是來源于FM的欄目類。”
此外,對于音像類出版企業而言,這更是一個發展契機。借助互聯網平臺,將其多年累積的資源以更有效地方式傳遞出去。湖南電子音像出版社成立了樂聽網,用戶可以在這個網站上直接收聽該社的有聲書,如“聆聽經典”系列歷時10多年打造而成,邀請了孫道臨、濮存昕等35位當代語言藝術家參與錄制,共有40張CD,長銷不衰。2015年3月,該社開發的“聆聽經典”APP在安卓市場和91市場上線。
商業模式多樣化,贏利單一
有聲書大勢正起成為共識,但我國有聲書市場起步晚,尚處于摸索階段,標準與規范都不夠齊全。如何破解有聲書的商業模式困局成為業內外人士的關注點。
據于琦介紹,有聲書產業鏈由作品(版權)、音頻轉化、平臺(渠道)、用戶四個環節構成——獲取作品文字版權之后,進行音頻的錄制轉化,把成品推到平臺和渠道,最后由渠道推到用戶,用戶反向回來需求內容,構成了相對完整的產業鏈條。各家形成自己獨有的商業模式。
據了解,國內已有多家出版社涉及有聲書制作,大多集中于童書領域,如北京出版集團“金色童年系列”推出“有聲親子睡前故事”4冊,江蘇教育出版社今年年初推出 “pi kids”有聲童書中文版。一些走在行業前端的出版策劃機構更是將有聲書作為其全版權經營的重要環節,如博集天卷、讀客熊貓、中信智匯和果麥文化等紛紛入駐喜馬拉雅、蜻蜓FM等聽書平臺,不僅拉動了圖書的銷售,還創造了新發展空間。中南博集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數字部總監鄒積川表示,在全版權運營時代,有聲讀物是一部作品非常重要的衍生版權。一開始博集只是希望通過聽書平臺把作品推薦給更多的讀者,后來才逐漸萌生做有聲讀物產品線的想法。據其介紹,此前博集和喜馬拉雅合作將張嘉佳《從你的全世界路過》制作成有聲書,推出“讀出你的睡前故事”,不到一個月PV訪問量就高達1.5億人次。而“法醫秦明”系列叢書,僅在喜馬拉雅上的獨立收聽用戶就超過了100萬。
而一些財力與實力兼具的大型出版企業,則并不滿足只是作為內容的提供商,而是更為深入,借有聲出版完成全版權產業鏈的整體布局——或是推出自有聽書平臺,或者借資本之力與內容優勢入股相關聽書平臺。早在2012年,中國出版集團數字傳媒有限公司就開始發力有聲書,成立有聲圖書事業部;2015年,推出聽書APP“去聽”,集有聲讀物收聽、下載、分享和資訊等服務為一身。目前,中版數媒公司有聲事業部的自有版權有聲產品已超過6000小時,未來還會與一些合作平臺共享版權。不久前,青島城市傳媒以6000萬元入股喜馬拉雅互聯網音頻平臺,并以青島出版社優質版權內容、作者資源為核心,在美食生活和少兒書刊領域與喜馬拉雅展開獨家合作。
縱觀整個有聲書市場,贏利模式還是較為單一,基本是線上下載、收聽付費或線下實體出版發行或預裝進硬件隨終端一起銷售。對此于琦表示,C端付費(用戶付費)的條件開始逐步成熟,用戶付費的模式會漸漸走俏。但各個渠道以及各家的資源不同,各家有聲書盈利模式也是不同的。據悉,目前酷聽聽書、喜馬拉雅、蜻蜓FM等主流音頻平臺已經逐漸開始推廣付費內容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出版企業則是走終端路線,這為其帶來了不錯的收益。據北京鴻達以太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林江發介紹,鴻達以太有聲書運作方面,一個重要的模式就是“內容+平臺+終端”,把所有內容放到云平臺上面。他表示,目前鴻達以太計劃推出一個高品質的評書機,有聲書版的kindle,讀者可以通過該評書機隨時收聽其鴻達以太制作的有聲書。目前,該評書機在兩天內便眾籌了10萬元。
火熱背后瓶頸待突破
有受訪者對記者表示,目前有聲書市場看似很火熱,但只是外表熱鬧,大多數有聲書平臺都還處在“輸血”狀態,并未實現真正的盈利。一方面成本過高、收益太少,另一方面版權糾紛不斷,盜版問題嚴重,導致有聲書未能形成有效的盈利模式。
“成本太高,但收益太低”,一位受訪者對記者吐苦水。記者了解到,不算版權費,一種有聲書的制作成本上千元。有些企業為實現內容精細化制作,買了版權后由編劇團隊編輯劇本,由導演團隊分角色,再由后期制作音效,由40多人組成的專業演播團隊共同完成一部作品的錄制。據了解,中版數媒公司已經建立了兩個專業的錄音間,未來有聲書在內容改編、后期制作等各環節都會全程控制,保證專業級別,做出的內容可直接提供給廣播電臺。但是這些有聲書的定價卻很便宜,如“去聽”上經典名著《了不起的蓋茨比》其定價才3元,這就意味著如果沒有大量的用戶購買,就會虧本。這種成本與收益不對等制約著有聲書行業規模化發展。
與電子書類似,盜版問題也成為制約這一行業發展的重要瓶頸。對此,于琦深有體會,“我們公司是從2012年開始依靠廣播劇做用戶付費,當時也取得了不錯的收益,很不幸2013年就停掉了,因為眾多的盜版平臺打敗了我們”。他表示,如果不解決盜版問題,根本無法讓用戶真正形成付費的習慣。
而在這背后既有國人版權意識不夠的問題,也有企業對版權的認識不到位的問題。北京東易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趙虎律師表示,有聲書版權不僅包括作者的或者著作權人的著作權,還有表演者權利。其中著作權方面共有17項權利,其中4項是精神性權利,還有13項是經濟性權利;而在表演者權利方面,則是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權利,現場直播或者表演的權利,錄音、錄像的權利,以及信息網絡傳播權。只有獲得這些項授權,才算真正獲得有聲書的版權。
而這也是一些傳統出版商至今仍對有聲書持觀望態度的原因。不過值得高興的是,一些聽書平臺已經對版權保護采取實際行動,如酷聽聽書建立“版權管理系統(CMS)”“錄制管理系統(ACE)”,通過這兩個電子系統來保障有聲書的版權。于琦表示,“不管是輸出也好,還是使用也好,至少在權利范圍之內我們是做正版。”中文在線推出版權資產管理系統,悅庫也推出類似的管理系統。此外,一些運營商、出版社、文學網站還共同參與設立了“中國聽書作品反盜版聯盟”來推進聽書行業的正版化進程,并在國家監管部門的支持下,構筑聽書行業的新秩序,有效保護聽眾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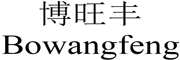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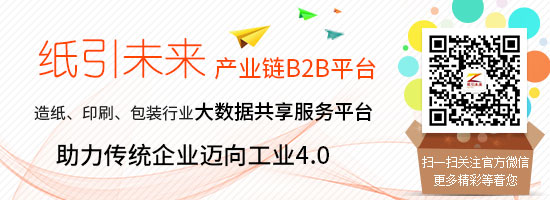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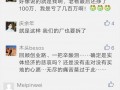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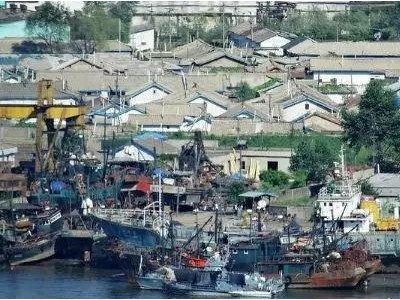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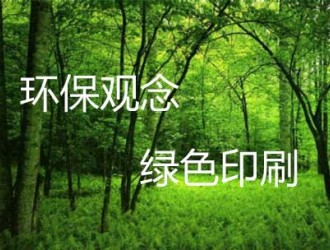


 紙友
紙友
 行情
行情
 訂單
訂單
 廣告
廣告
 找貨
找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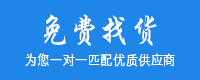
 簽到
簽到

 關注
關注
 客服
客服 TOP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