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定西大街90號原印刷廠業(yè)務承印所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舊廠門

? ■上世紀九十年代職工正在操作四色膠印機

■壓膜車間的工人正在緊張地工作

■制版車間內,工人細致地查看膠版

■幾位印刷機長正在比色

■裝訂車間內的工人正在工作

■廠內舊廠房的細節(jié)顯示著該廠的悠久歷史

?■印刷大廈
■神主畢升伴妙音? 模糊歲月尚堪尋
公元105年,東漢蔡倫“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改進了造紙術。紙張的徹底變化讓印刷術的創(chuàng)造成為可能,唐代,印刷術始有,但不便捷。直到北宋畢升創(chuàng)造了活字印刷術,一個改變和推動世界文明發(fā)展進程的里程碑式時刻由此出現:南宋周必大按照畢昇活字印刷辦法,使用膠泥銅版,成功刷印了《玉堂雜記》;元代王禎發(fā)明了木活字印刷法,清乾隆年間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則是我國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一次使用木活字的印書;從十三世紀到十九世紀,活字印刷術傳遍全世界……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演員翩然起舞展現活字印刷術的精彩演出,驚艷全世界。泱泱華夏大國的文明進程中,始終能尋覓到印刷術留下的印記。
以上是記者在去印刷一廠采訪前,先補習的一些關于印刷術的知識,非常粗淺,亦是皮毛。但終究對“印刷術”的社會價值有了些許認識,帶著發(fā)現和探秘心理,記者踏上了對印刷一廠的尋訪之旅。
印刷一廠位于保定市蓮池區(qū)瑞祥大街,采訪時正趕上修路,道路封閉了一半,人車通行凸顯逼仄。記者驅車小心行駛,進入廠區(qū)后眼前豁然開朗,風景也陡變:老舊的紅磚房夾雜于現代高樓之中,稍顯古樸陳舊;五、六十年代建起的廢棄鍋爐房帶著年代痕跡孤獨聳立,無言訴說著歷史滄桑;甬路兩側古樹參天,綠蔭如蓋遮擋著初秋的艷陽;職工食堂也顯露出上個世紀的風貌,高大房梁配水泥地面;先進的印刷機發(fā)出轟轟鳴響,偶有著工裝的工人們出入穿行……廠區(qū)內漫步,總有這樣混含著現代文明與歷史軌跡的景致撞入視野,讓人禁不住產生時空幻化的錯覺,不知身處何處。回神細想,這大概就是印刷一廠經過歲月沉淀、浸染后所生發(fā)出的天然氣質吧,渾然天成,和諧統(tǒng)一,卻又隱藏了無數值得追尋的故事……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
查訪印刷一廠的前世今生會發(fā)現,它從初創(chuàng)到發(fā)展壯大,周身遍布著濃郁的“紅色血液”,與國家危難、民族振興息息相關。
印刷一廠1938年9月10日始建于任丘縣陳王莊村,由新華印刷廠和抗戰(zhàn)學社共同演變而來。工廠的誕生復雜而多變,卻又在支持抗日戰(zhàn)爭宣傳、打擊日寇侵略上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37年7月,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冀中地方黨組織領導的抗日武裝和呂正操率領的部隊回師冀中,使冀中地區(qū)抗日戰(zhàn)爭迅速展開。1938年夏天,中共冀中區(qū)黨委書記黃敬提出要創(chuàng)辦區(qū)黨委機關報——《導報》,并責成冀中抗聯主任史立德、“抗戰(zhàn)學社”社長路一負責籌辦事宜。為了快速配備人員和機器,籌備組當即把在安平地區(qū)出版《抗敵報》的印刷廠工人和全部鉛印設備轉移到任丘縣陳王莊,調撥給《導報》社使用,9月10日,《導報》社、印制《導報》的新華印刷廠、青塔書店、抗戰(zhàn)學社同時掛牌宣告成立,印刷一廠雛形就此誕生。
當時的新華印刷廠主要任務是印刷報紙,有時也印刷黨的文件和資料。全場職工100多人,廠內設有鑄字、排字、鉛印、零印、裝訂等工序,工人們每天除了揀字、排版外,還得搖機器輪子搞印刷,當時沒有電,機器只能用手搖,搖動巨大的印刷機常常讓工人們體力消耗很大。工人們在工作時,常常聽到外面槍聲陣陣、炮聲隆隆。但大家只要想到能為抗日戰(zhàn)爭出力,渾身上下都充滿干勁兒。耄耋之齡的離休干部何永安回憶起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時,仍感慨不斷:“抗日戰(zhàn)爭時期,職工們是真拼呀。吃糠咽菜、挨餓受凍都是小事,每個人都做好了隨時犧牲的準備。”
隨著抗日戰(zhàn)爭進入持久戰(zhàn)階段,印刷一廠也開始了游擊印刷、地下印刷的特殊時期。何老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依然清晰記得民族存亡之際印刷企業(yè)職工不畏生死的頑強堅守。“日寇對冀中根據地進行‘大掃蕩’期間,報社和印刷廠成為敵人重點摧毀的目標,一個多月時間印刷廠就隨著冀中機關多次轉移,有時大家剛安裝好印刷機器,敵人就開始掃蕩,工人們又馬上拆卸機器撤離,印好的半成品也拉著一起‘跑’。那時,每個工人都練就了摸黑拆裝機器的真本領。為了游擊印刷,7人分包一臺機器,每名工人背一背包隨軍游擊,利用行軍間隙刻版印刷報紙。有時沒有油印機,就借老鄉(xiāng)家的大鏡子或小學生用的石板當調墨板,再借裁衣的尺子卷住蠟紙的一頭就開始印刷。后來,游擊印刷越來越難,冀中區(qū)黨委又建立了石印廠,在村莊之間的偏僻大洼中挖地窖印刷,給工人、交通隊配發(fā)了槍支,遇敵‘掃蕩’時,就埋藏洞口,轉移人員,敵人一走,立即恢復印刷。”
印刷職工用這種舍生忘死的犧牲精神保證了《導報》的印刷出版,為冀中抗日積蓄了無窮精神力量,“那時,群眾們拿到報紙后都如獲至寶,奔走傳播,人們知道黨仍然領導大家堅持抗戰(zhàn),鼓舞了斗志,增強了必勝信念。”何老說:“群眾的期待是印刷職工冒著生命危險印報紙的強大精神動力。” 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印刷企業(yè)職工為打擊日寇、宣傳抗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結束后,印刷一廠才從動蕩中徹底“新生”。1949年3月,印刷一廠搬遷至保定南關,工廠更名為“河北印刷廠”,職工約200人,印刷過程開始使用電力,但裝訂工序仍大都采用手工操作,企業(yè)年生產能力達到8000令紙。從此,印刷一廠作為冀中區(qū)新聞出版事業(yè)的有機組成部分,完成了戰(zhàn)爭期間的歷史使命,踏上了和平時期國家建設發(fā)展的新征程。
■千淘萬漉雖辛苦? 吹盡狂沙始到金
印刷一廠度過了戰(zhàn)爭時期的艱難歲月,沐浴著新中國成立的曙光,以百倍激情投入到企業(yè)建設中去,從建設初期的百廢待興,到發(fā)展中期的成績斐然,半個世紀里,它始終如一株傲然挺立的毛白楊,在河北印刷業(yè)的沃土上茁壯成長、抽枝散葉,孕育出勃勃生機。以不斷自我突破之勢完成了破繭成蝶的蛻變,欣欣然迎來了屬于自己的“黃金時代”。
遷入保定市后,印刷一廠曾經歷數次更名,一次搬遷,每次調整都為企業(yè)帶來了發(fā)展?jié)撃堋?950年11月,河北人民出版社與印刷一廠合署辦公,工廠更名為“河北人民出版社印刷廠”。此后,工廠更新設備,從上海引進技術人才,到1958年秋季,工廠停止對外承攬業(yè)務,全面承擔印制河北省中小學課本和河北人民出版社本版圖書的任務,印好課本成了企業(yè)生產的“頭等大事”。
在離休干部張鋼瑞家里, 88歲的張老說起當時的情景還滔滔不絕,“開始工廠印刷能力有限,絕大多數課本印不了,都是讓北京、天津等地大型印刷廠代印。企業(yè)領導著急了,總這樣可不行,得想辦法呀。于是,1960年,經過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同意,工廠與北京西四印刷廠合并,西四印刷廠130臺印刷設備、219名職工都從北京遷來保定,企業(yè)規(guī)模壯大不少。”據印刷一廠廠志記載,“到1966年,印刷一廠已經擁有制版、鉛印、裝訂、膠印等6個生產車間,成為一個綜合性印刷廠。全省50%的中小學課本印量都能獨立完成。”
1978年12月4日,印刷廠再次更名,廠名變更為“河北新華印刷一廠”。此間,印刷一廠還完成了一次搬遷,從保定南關搬到了原河北省體育專科學校舊址,為什么要搬遷?張鋼瑞老人說:“因為廠子所處的南關地址,東、西、南三面均比廠區(qū)地勢高兩米以上,每逢雨季,廠區(qū)內雨水倒灌,積水滿地。1954年8月,保定連續(xù)下暴雨,廠區(qū)進水達1米多深,機器設備被淹,職工全部抗洪搶險,企業(yè)被迫停工半月。1963年,保定發(fā)大水,企業(yè)再次遭殃,損失巨大。為此,1965年5月,在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大力協調下,企業(yè)整體搬遷。從那以后,職工們再也不怕下暴雨了。”
搬進了新廠區(qū),有了新廠名,伴隨著改革開放清晰的號角聲,印刷一廠走上了發(fā)展快車道,迎來了屬于自己的豐收季節(jié)。
收獲是在不斷自我完善和不斷改革中完成的。1985年,企業(yè)陸續(xù)實行廠長負責制、工資總額同上繳利稅掛鉤的承包經營制等,從計劃經濟開始向市場經濟試水,企業(yè)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進入20世紀90年代,企業(yè)開始廣開門路辦三產,建立造紙廠、設立實業(yè)公司和附屬加工廠等,企業(yè)效益節(jié)節(jié)攀升。“有錢”后,印刷一廠陸續(xù)引入國外先進設備擴大生產,到1995年,企業(yè)年生產能力達到制版2萬塊,照排1.5億字,書刊印刷55萬令,書刊裝訂65萬令,承印了省內及天津、北京等30多家出版社的黨政、科技、文藝書刊、商標廣告等業(yè)務,1996年,印刷一廠有217種產品被國家新聞出版署印刷產品質量監(jiān)督檢測中心認定為優(yōu)質產品,截至1998年年底,企業(yè)已成為擁有1400多名職工,6個生產車間,3個輔助車間,擁有國內外86臺(套)先進設備的大企業(yè),產品質量達到國內先進水平,成為河北印刷業(yè)的翹楚。
在企業(yè)鼎盛時期,保定市民對印刷一廠的各種新鮮事均津津樂道。那時,職工宿舍、職工食堂、幼兒園、招待所、浴室、理發(fā)室、茶爐房在企業(yè)里一應俱全,職工不出廠區(qū)衣食住行全能解決。青年職工王曼雖沒見證過當年企業(yè)的輝煌,但她的姥爺、姥姥,兩個姨和舅舅都是印刷一廠的職工,親戚們總給她講企業(yè)紅火時的情景:“各種福利都有,企業(yè)啥都管,那時候好多公務員都搶著調到我們企業(yè)來上班。那時候,印刷一廠的職工走在大街上各個腰板挺直、春風拂面。”從小在廠區(qū)宿舍大院里長大,王曼對這里充滿感情,她大學畢業(yè)后毅然走入企業(yè),成為印刷一廠的一員。
2000年8月,印刷一廠標志性建筑“印刷大廈”正式投入使用,記者采訪時看到,大樓歷經風雨,有些墻面已斑駁,大廈早沒了當年的恢弘氣勢。但記者仍能從總建筑面積33331.1平方米,建筑高度23.95米,可容納制版、印刷、裝訂等各工序車間的文字簡介中體味到大廈曾經的卓爾不凡。辦公室工作人員說:“印刷大廈可是當年我省同行業(yè)中數一數二的綜合性建筑。”如今,作為時代符號,它已成為職工們內心無法磨滅的記憶。
■博觀而約取? 厚積而薄發(fā)
海明威在代表作《老人與海》中借用捕魚老人圣地亞哥的口,寫下了這樣的話:“人可以被毀滅,卻不可以被打敗。”這句“勇者”宣言,打動了全世界無數人。
印刷一廠作為我省印刷業(yè)龍頭企業(yè),它榮耀過、成功過,對未來,企業(yè)也報有美好遐想。但現實總是殘酷的,進入21世紀,印刷業(yè)市場競爭加劇,曾經傲視群雄的行業(yè)巨頭不斷感覺到競爭壓力,企業(yè)經營幾遇難關。怎么辦?是故步自封、維持現狀,還是勇敢去商海中搏擊一番,印刷一廠果敢選擇了后者。方向定了,就要落實行動,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于是,一幕現實版《老人與海》在印刷一廠上演。
從2005年起,企業(yè)決策層開始修正經營方略,增強市場應變能力,在計劃外業(yè)務方面大做文章。企業(yè)定下“規(guī)矩”:一方面抓好固定刊物、外埠教材、教輔等長期業(yè)務,保證客戶不流失;一方面拓展埠外市場,開發(fā)國外印刷市場,增加商業(yè)印刷和包裝印刷的市場業(yè)務量。“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全廠職工凝心聚力,上下一心,將經營決策一以貫之,幾經努力,印刷一廠這艘大船再次揚帆遠航。
9月底,記者在企業(yè)車間采訪,看到一家著名食品企業(yè)的方便面外包裝正由印刷一廠承印,每天數萬個色彩鮮艷的外包裝彩膜從流水線上“走”下來,被工人整理打包后運往外省。
時光荏苒、白駒過隙,十數年,印刷一廠用持之以恒的堅守和創(chuàng)新,迎來了自身發(fā)展的涅槃重生。如今,企業(yè)在書刊、包裝、塑印三個領域齊頭并進,再做行業(yè)先鋒。今年,印刷一廠還將搬遷新址——河北數字印刷產業(yè)園(保定基地),產業(yè)園包括出版發(fā)行、印刷復制、科技開發(fā)和產業(yè)物流四大功能,職工們的工作區(qū)實現了自動化和信息化的管理流程,可以實現從印刷產品的出版源頭到裝訂運輸的一條龍服務,是我省最具規(guī)模的數字印刷產業(yè)加工基地。與此同時,與職工們相伴半個世紀的老廠區(qū)也要徹底退出歷史舞臺了。許多老職工都對此依依不舍,何永安老人說:“搬遷前還要回廠里看看,我這一輩子都和印刷一廠有關,青春、奉獻、熱愛……所有的一切都讓我刻骨銘心。”而對搬遷后的現代化新廠區(qū),許多職工也充滿期許,年輕的車間主任王冬表示:“在科技化新廠區(qū)里,我要和工友們一起勤奮工作,希望能見證印刷一廠新的騰飛。”
無論舍與不舍,有些結果總是無法拒絕。就像年初黨委書記、總經理王樹青在新年獻辭中告訴所有職工的:“企業(yè)要在探索中行進、在創(chuàng)新路上追尋、在自我完善中覺醒、在體制變革的利刃下破繭成蝶。”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帶著對未來的篤定,讓我們期待,印刷一廠在發(fā)展的新征途上能再創(chuàng)佳績、再續(xù)輝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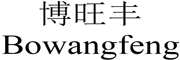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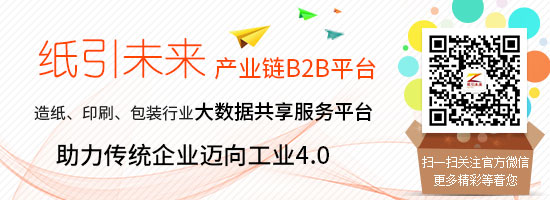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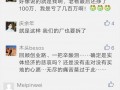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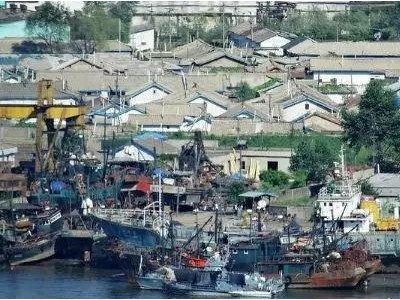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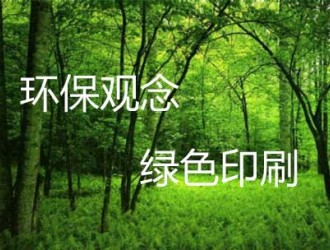


 紙友
紙友
 行情
行情
 訂單
訂單
 廣告
廣告
 找貨
找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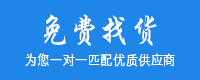
 簽到
簽到

 關注
關注
 客服
客服 TOP
TOP

